|
禅不行说;禅,完满是一种小我私人的体验,而对禅的体验又不能像其他的常识那样在师生间用口和笔墨加以授受,这就是禅门中素来以为有禅而无师的原理。于是,就有了呵佛骂祖者,就有了烧佛取温顺者,就有了面临祖上的圣典拂衣而去的凛然正气,因此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一个个精巧禅师的人品魅力。 劈下的利剑,在猝不及防中斩断了凡夫的执着之念,砍断了那些执着于理念的学人们精力上的各种拘束。而普愿本身也经常以刀来譬如本身。听说有一次外地求法的和尚前来问路,恰遇普愿在野地割草,当那问路的和尚问怎样去南泉院,谁是普愿禅师时,普愿没有正面答复那位问话的和尚,而是举起了手中割草的镰刀:看到这刀子了吗,我就是啊。 禅是无法用笔墨来表达的,正所谓“一说即是错”。作为“王先生”,普愿生平的教训就是要让学人们丢掉统统执着之念,用本身心意去熟悉事物。为了到达这一目标,普愿这把尖利的刀子不吝做出被其后的无数人驳倒纷歧的杀生举动,这就是著名的南泉斩猫。在那些执着于外界事物的凡夫眼前,统统有形的事物城市成为障蔽心意的桎梏,以致一草一木,一线一针。于是,就产生了对象两堂和尚争夺一只猫儿的闹剧。对付那些连一只猫儿也不愿放下的和尚来说,又何谈独具伶俐和人生的脱节呢?于是,当两堂的僧工钱那只可怜的猫儿争吵不休的时辰,普愿毅然决然地做出了斩猫的举措。执着的工具消散了,“统统有相,皆为虚妄”(《金刚经》偈句),学人们执着外相的意识也在这刀光血影中警觉了。在普愿看来,所丧失的是一只无辜的猫,尚有本身被无数人指责的杀生的罪名,但他却认为,能让对象两堂以致其后无数的学人以后警觉,那是比什么都合算的。普愿让人们分明:凡事不行执着,最要紧的,照旧要像刚好前来的赵州一样,将本身的鞋儿顶在头上扬长而去的超然物外的人生立场。这正如日本学者铃木大拙老师所言:禅不是修养,禅是要把统统拘束彻底抛却。(《禅者的思索》)。 在南泉普愿心目中,统统现成的端正都是民气的拘束,人必需突破传统的樊篱,将无穷盈然的心意揭示出来,以建立本身独立不倚的精力风致。当一位和尚以供手站立的姿态向他问候的时辰,普愿鄙夷地说他“太卑鄙”,而那位不知所措的和尚又改为双手合掌向先生问讯时,普愿又说他“太僧气”。普愿大概简直很瞧不起这位除了卑鄙即是僧气的和尚,普愿必然在内心说,莫非你就没有你本身的方法吗? 三 太和初年(827),宣城(今安徽宣州市)廉使陆亘因敬慕南泉普愿独行众人的人品精力,遂与护军彭城刘济一路恭请他下山说法,师事星期。 听说陆亘在宣城一带多有善政,而对禅法也异常热衷。然而他事实是一个被无数理念贯注得有些麻痹的士医生,他所热衷的,是笔墨上的教条,是理念上的执着。这也是中唐往后中国禅流于情势的广泛征象。一次,当陆亘请普愿来家中做客时,陆亘指着院子里的一块大石说:这块石头,学生偶然坐在上面,偶然躺在上面,但我此刻又想把它雕成佛像,先生说行吗?普愿说:“行啊。”陆亘暗示猜疑,这曾被本身的身子轻渎过的石头真能镌刻成一尊纯洁的佛像吗?于是他说,生怕不可吧?对盖卸熄的执着,普愿只好说,不可不可。在普愿看来,石也好,佛也好,都不外是一种外在的情势,木佛可以烧火取温顺,顽石虽然也可以镌刻成佛像了,行与不可,又有什么不同呢? 陆亘对笔墨禅的执着还不止云云,一次他不知又从哪儿掉来一只大大的书袋,他问普愿:“昔人瓶中养一鹅,鹅徐徐长大,出瓶不得,现在不得毁瓶,不得损鹅,师父您奈何让鹅出瓶?”日本的禅学者铃木大拙说,这其实是一个天大的困难,不毁瓶又不损鹅,生怕那鹅永久也取不出来吧!究竟上,被养于瓶中而收支不能的非是一只假造的肥鹅,而是被禅的理念约束得近乎呆痴的陆亘医生。于是,普愿再次挥动起他那柄利剑,溘然大唤:“医生!”陆亘应声而答。南泉兴奋地说:“出来啦!”陆亘给本身配置了一个陷阱,南泉一声呼喊,把一时陷入头脑空缺的陆亘从陷阱中挽救出来。听说陆亘挣脱了相对前提的约束,他开解了。这不禁使我们想起昔时四祖道信向他的先生求得解缚之法时僧璨所说的话:约束你的,本来是你本身,而非他人,因而脱节本身的还是本身,正所谓解铃仍需系铃人。 普愿在他长达八十六年的人生中不只建设了南泉禅院(道场),从而让中国的农禅制度得以扩大和升华,在其生平的弘法中,更是创作了一系列语录(公案),使之成为中国头脑文化史上一笔名贵的精力财产。宋《高僧传》收录了他的传记,《景德传灯录》、《碧岩录》、《从容录》、《无门关》、《五灯会元》、《葛藤录》等各类禅宗文籍都别离收录了他的传记和语录。感激这些不立笔墨的笔墨,由于它事实让我们从这些笔墨中感觉到一千多年前一位精巧禅师的人品魅力。 (责任编辑:admi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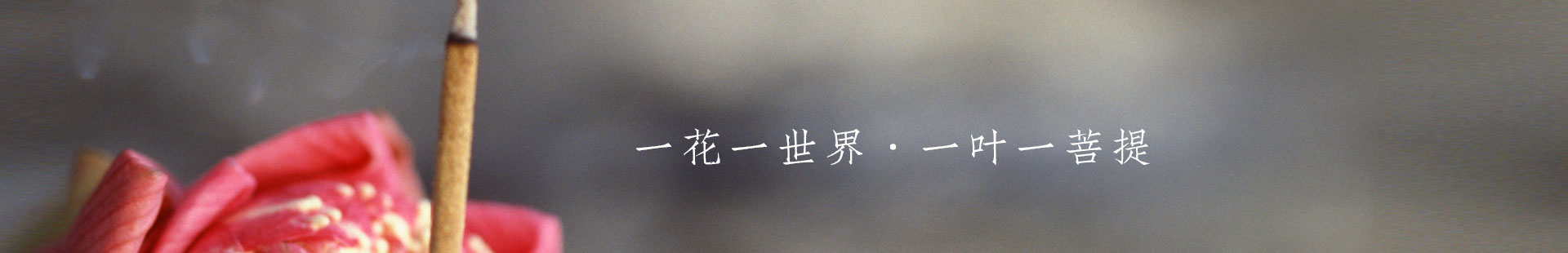
南泉普愿的人品魅力(2)
时间:2016-08-28 11:08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网络 点击:
次
禅不行说;禅,完满是一种小我私人的体验,而对禅的体验又不能像其他的常识那样在师生间用口和笔墨加以授受,这就是禅门中素来以为有禅而无师的原理。于是,就有了呵佛骂祖者,就有了烧佛取温顺者,就有了面临祖上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 发表评论
-
- 最新评论 进入详细评论页>>
- 栏目列表
-
- 推荐内容
-
- 南昌双胞胎的同命异报
南昌双胞胎的同命异报...
- 将军和士兵
将军和士兵...
- 一双手的姿态
一双手的姿态...
- 练出值百万美金的笑容
练出值百万美金的笑容...
- 苹果的两种分法
苹果的两种分法...
- 割草男孩的故事
割草男孩的故事...
- 南昌双胞胎的同命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