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一起等待火车的来临。 这是一个不知名的小站。几分钟前我们刚刚来到这里。 “我们”是谁?我不知道。我一时想不起身边的这些人是谁。但是我相信:他们或许应该是和我十分接近的人。人在处于极度慌乱的时候,是不容易对自己和身边的状况作出清楚的判断的。我想“我们”最起码有三个人,只有一个人我记得很清楚,那就是你。就在数分钟前我们为了逃避某些可怕的东西而来到了这里。 那些可怕的东西是什么?我仍然不知道。或许是一大群蝗虫;或许是一支军队,或许只是一条看上去并不怎么凶恶的狗,就像小时候邻家猎人养的那条气喘吁吁的小猎狗一样。我们则像是几只被击伤后仓皇低飞的鹧鸪。 我看见自己的衣裳沾满了尘土,我的鞋的前端开裂了,这双鞋已经很老了。我抬起脚尖,光线照不进裂口里去,显露出一片幽深。从这片幽深里我的思维慢慢地变得清晰起来,我记起了我们是怎样从那个山坡上“溜”下来的,这个山坡现在看过去显得很远。我记起了我是怎样拉着你的手从那上面溜下来的。是的,你的手很瘦弱纤细并且无助,还有你的目光。 我记得我急急地对你说,快来吧,我们一块儿下山。因为除了下山我们没有别的选择,素食,尽管山坡是那样地陡峭。你没有作声,但你看上去真的很美。我牵住了你的手,我感到你抓紧了我,我们就这样紧紧地吸附在一起,因为我知道,我也不强壮。 我们的鞋底摩擦着坚硬而凹凸的山石,强大的惯性让我们无法停驻脚步。我们像坐滑梯一样地快速往下,没有快感,只有不可预知的恐惧如影随形。尽管到现在我们也无法断定那究竟是什么,我是说恐惧。中途我们不可避免地摔倒过几次,你不容我伸手就迅速地爬了起来,有几次我都觉得摔得很疼,可是你没有吭声,继续往山下那两条发出依稀光亮的铁轨的方向赶去。 现在我不仅看见你的一只鞋子失踪了,袜子上满是大小不一的破洞,我还发现你的一只肘弯上的皮擦破了,渗出淡淡的血水,而你似乎也在打量着我。 对了,我忘了提到胖子,因为我会儿我看见了他。他站在你的身后,贪婪地窥视着你。他的脸上粘杂着尘土与汗水,嘴里还衔着三张车票。他的惊惶显然比他的贪婪更明显。 刚刚跑进破旧的候车室的时候,那个售票员木讷地坐在一张桌子后面。他喃喃地说,两班车差不多都要到站了,都是经过L镇的。奇怪的是他怎么知道我们要去那个小镇? 农民们拥挤着跑向月台。我下意识地伸出手来拉你,你却怔了一下并把手拘谨地藏到了身后,像一个胆小的孩子。可是旋即又慢慢伸出手来,拽住我衣服的下摆。于是我们一起往月台上跑,我感到你拽得很紧。 可是月台上并没有火车。一大群人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胖子回过头来,他的眼里满是绝望。我说,大概又要晚点了。没有人对我的话作出反应,因为连我也不知道火车是否真的是晚点,或者永远也不会来了。我回头看你,你的手还是拽着我的衣服,你的表情依然无助但却平静。我看见农民们匆匆地越过铁轨,向对面的月台跑去。胖子也顾不上瞧你,跟了过去。我把手轻轻拢在你的腰际,说道:我们走吧。你没有逃避,你看着胖子的背影越来越远,你的眼里掠过一丝哀怨,我听见你发出轻轻的一声叹息。一阵温度从与你接触的那个部位传递过来。我们慢慢走向对面。 汽笛终于响起。一列火车从远处驶近。周遭响起一片欢呼——难道农民们也是逃避着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你的眼里有什么在闪动? 胖子伸出手指成“V”字状,人差不多要跳到半空中,嘴里啊啊地叫喊着。我搂紧了你。 火车驶近了。可是火车终于还是没来。伴随着巨大的轰鸣驶过的只是一个火车头,这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两个迫不及待拦在车头前的农民现在蜷卧在十多米开外的铁轨边,我看见他们的灵魂像空气一样融入到空气中。抬头看天,天是灰的,无比坚硬。 “这里怎么没人管!!”胖子哭着喊道,人群漠然无声。我感到你在靠近我,身子像一片树叶一样微颤着。胖子是不会注意到你的眼里掠过一丝鄙夷的。与此同时,我嗅到你发际的那朵野花的香味。 “抱紧我!”你小声而又坚决地说道。 黄昏的时候,售票员斜倚在椅背上睡着了。一滩清亮的口水垂落在他肮脏的制服胸前。窗外,阴冷的风在一遍遍翻动着他面前的值班日记,那上面记录了小站建成以来最晚的两次晚点,一次半小时,另一次两小时,发生在同一天,都是往L镇方向的列车。 我们终究没赶上那两趟火车。是我和你。胖子最终和农民一起离开了。我们留在了这个小站简陋而空旷的月台上,看着第二趟晚点的列车缓缓地从我们面前驶离。 在这个小站上,我知道我们今生永远无法赶上从这里经过的任何一趟列车了,但是我们清楚地知晓:我们一起等待火车的来临,我们再无须恐惧和害怕。 (责任编辑:admi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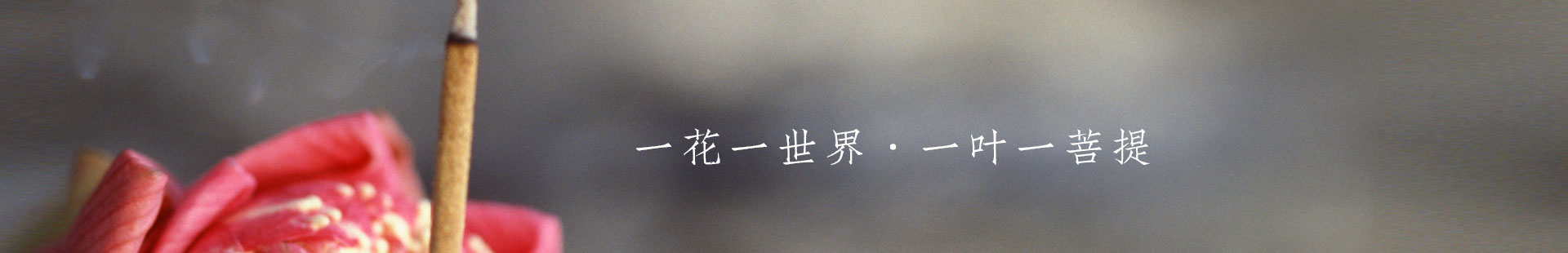
我们一起等待火车的来临
时间:2016-09-13 23:19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网络 点击:
次
我们一起等待火车的来临
顶一下
(0)
0%
踩一下
(0)
0%
------分隔线----------------------------
- 发表评论
-
- 最新评论 进入详细评论页>>
- 栏目列表
-
- 推荐内容
-
- 南昌双胞胎的同命异报
南昌双胞胎的同命异报...
- 将军和士兵
将军和士兵...
- 一双手的姿态
一双手的姿态...
- 练出值百万美金的笑容
练出值百万美金的笑容...
- 苹果的两种分法
苹果的两种分法...
- 割草男孩的故事
割草男孩的故事...
- 南昌双胞胎的同命异报
